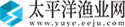湖南的雨霸蛮、泼辣、热情。
 (相关资料图)
(相关资料图)
故乡的雨和故乡的人一样,霸蛮、泼辣、热情。组图/吴琳红
故乡的雨是霸蛮的,它有一身的蛮劲。有时候,不分场合、不看时间,倏忽来了一面天那样大的乌鸦色的浓云,即便是中午,也把日头遮得严严实实。这时的雨是不会轻易下来的,必先任由它放出去的浓云遮天蔽日地大闹一番。
浓云翻腾着、滚闹着,毫不讲理地扩展着,将整个天空据为己有;又毫不客气地朝着地面压下来,把那些人们引以为豪的摩天大楼吞入腹中。这时候你如果站在高楼往天际看去,会看到天空在乌色浓云的操控下已经坠向地面;被浓云搅缠成一片混沌的地平线像一张无声怒吼的深渊巨口,将所触碰到的房屋、桥梁、凌驾于城市上空的高速公路鲸吞净尽,然后毫不留情地朝你席卷而来。光,是近乎无有的,云里的黑暗吞噬了它,就算是正午,也暗如半夜;风,是已然停歇了的,把天都压低了的沉重的大气压,是不会给风留出一丝空隙的。
你只能呆呆地站着,五指张开,按在落地窗的玻璃上,无需世界末日,就在这将下而未下的雨的面前,你已经知道自己如同这玻璃一样脆弱。
紧憋着,紧憋着,云的肚里蓄了太多的雨,已经翻腾不动了;气压也已经降到了最低,逼得人类时不时就得伸长脖子大喘一口气。着实憋不住了,那雨终于如同难产的婴孩一般“哇”的一声喷薄出来。它憋得实在太久,所以将那一肚子憋闷的怒火,朝着大地喷射。没有人可以在它的怒火中停留,每一滴雨都像一个耳光,扑头盖脸地打,打得人站立不稳,打得树木枝断叶落,打得方才开放的花瞬间凋落。
在这种决了天河大堤的、愤怒的狂雨中,自然界是沉默的——没有鸟敢叫,没有蝉敢鸣,没有青蛙敢在这种雨里鼓噪,只剩下那些没有魂灵的蠢物在挑衅——塑钢雨棚乒乒乓乓一顿狂响,停于其下的电动车也附和着“呜哇——呜哇——”地怪叫起来。
这样霸蛮的狂雨,如果下在春天,必会请来银蛇一般的闪电,在黑暗的天空中狂舞一阵,再放出几个炸雷助兴;如果下在夏天,一定带上一筐雹子,瞄准谁家新车脆弱的引擎盖任性地掷;如果下在秋天,必须趁着秋风大作,赶上前去,将伞掀翻,转瞬之间就把人浇个透湿;如果下在冬天,一定要将你的鞋袜裤脚浇湿,让你在蚀骨的寒冷中煎熬。
故乡的雨是泼辣的,它一下就要下个痛快。明晃晃的大太阳天,人们坐在饭铺子前的空地上吃喝着,雨说来就来了。没得报信的,阳光和风都是它的同谋。小孩巴掌大的雨点子兜头浇下来,砸在地上,溅起一团暑气;砸在人头上、身上,吓得人端起饭碗就往屋檐下跑。人们伸头往天上看,没有云,这种泼皮破落户来的时候从不驾云。
故乡的人把这种雨叫作“太阳雨”,你说它泼不泼——太阳还挂在天上呢,它就这么稀里哗啦一顿下了,不带半点犹豫。下完了,走了,有时候随手放一段彩虹,让你们这些人大惊小怪去。
这雨还有个令人无奈的恶趣味——喜欢赶在上下班高峰期一顿下。本来马路就已经不堪重负,人们的神经也绷得梆紧,但它不管,它就要来凑热闹。听到那些挤成一团的大车小车在它制造的雨声中焦急地按着喇叭,看着那些赶着上班、回家的人用手挡着头顶在路上狂奔,溅起的水花一串串地甩到人们的裤腿上、屁股上,雨哈哈大笑。人们当然会咒骂不已,雨把头一扭:“我就要下,下得痛痛快快,你们管得着吗?”
当然,除了霸蛮、泼辣,故乡的雨也是热情的,它毫不吝啬,年年岁岁有求必应。大多数的春天,它都是润如油的,它温柔、绵长、细腻、轻柔,如烟如雾一般地下着,下在水稻田里,下在灰蒙蒙的城市里,下在薄雾朦胧的东江湖上,下在烟波浩渺的洞庭湖里。
有时候你都不觉得它是雨,只觉得它像一层纱,由针脚一样细碎的雨滴形成的雨纱。这雨纱笼罩天地,又随风飘摇,将遥遥一碧的东江湖渲染成一幅雾气蒙融的水墨画。在这斜风细雨中,飘然轻舟上,身着青箬笠绿蓑衣的打鱼人抛出一方渔网,江水荡起涟漪来。
雨中的东江是如梦如幻的,而雨中的洞庭湖则是浩渺如烟的。只有见过雨中的洞庭,才能懂古人“烟波”二字的巧妙、贴切。雨纱给湖中每一朵翻起的水波都罩上一层水雾。那水雾时浓时淡,水波翻涌,水雾便随之起伏,像佛堂里氤氲的香,那么缥缈、那么舒缓,勾勒出风的形状。
故乡的雨下着,下出了洞庭鱼米之乡;故乡的雨下着,淋着这样的雨长大的湖湘子弟霸得蛮也耐得烦;故乡的雨下着,下出了湖南人一片火辣辣的热情……
故乡的雨啊!